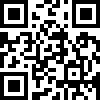1974年,我在太原市南郊区红寺村插队。到了秋天,大秋作物开始收割了,村民们忙碌着,这时也是给牛羊贮存青饲料的日子,叫做贮青。
贮青是把玉米秸秆放在一个方形坑里,就是青贮饲料窖,青贮饲料填满后,盖上土发酵,冬天里牛羊就可以食用了,玉米叶子大多还是绿的。白天,生产队长安排我们到成熟的玉米地里掰玉米。每人挎个筐,负责三四垄,一畦地有两三个人,大家齐头并进,不能落掉每一穗玉米,那可是庄稼人一年的心血啊。每株玉米上大多结两穗棒子,玉米装满箩筐送到地头,由生产队的马车、拖拉机拉到打谷场上。女劳力们剥掉玉米棒子皮,而后作为口粮的一部分,分给生产队的社员(村民)。剩下的生产队要向粮站交公粮,或作为村集体的余粮储存起来。
秋收是很紧张的,有的大秋作物收割以后,还要播种小麦,所以一到秋收就是每天四出勤,吃完晚饭还要出工,收割已经掰掉玉米穗的玉米秸秆。晚上收割玉米秸秆是2人一畦地,报酬是每人2分。第二天这些玉米秸秆拉回村里,更多的是卖给农牧场做青贮饲料,秸秆拉运要快,放得时间长了,就会脱水,做青贮饲料质量就差些。
农牧场,离我们村不远,每年要给奶牛做青贮饲料。村边有农牧场的一片饲料玉米地,种植密度大,结穗少。那地里的玉米远远不够,还要购买我们村的部分玉米秸秆做青贮饲料,村里等于“产品增值”,还能“劳力输出”,给农牧场把玉米秸秆收割好,送过去,这也是村里的一项副业。
那天,生产队通知,晚上男劳力通宵给奶牛场制作青贮饲料,我们知青跟随农牧场的卡车和村里的拖拉机搞运输。奶牛场的青贮饲料窖比我们村里的气派多了,平地上长宽几十米,六七米深,窖底平整,窖壁如墙。窖边灯火通明,三四台切秆机“哒哒哒”的同时开动,有人抱上玉米秸秆传送,有人往切秆机里送秸秆。秸秆连秆带叶切成几厘米后,碎秸秆就被抛入窖中。农牧场地里的玉米是不掰玉米棒子的,连秸秆带玉米穗全部切碎,对牛来说还增加了营养。社员们割完村里的玉米后,帮农牧场连夜收割,我们几辆卡车拖拉机连夜运输,每辆车上有三四人,跟车装卸。半夜时分,农牧场管饭,馒头烩菜,一个馒头二两,每人都要吃四五个,吃了饭继续干。到了下半夜,我们又困又乏,在运输的路上忍不住在车上打个盹,不时还有蚊虫叮咬。
朝霞微露时,地里的玉米收割完了,玉米秸秆也全拉回来了,青贮窖也满了,上面要苫上遮盖物,再盖上土,踩实,就大功告成了。玉米秸秆在青贮窖里,几周后就会发酵,青贮饲料气味酸香,柔软多汁,适口性好,营养丰富,冬天里,取出来就是奶牛的美味口粮。
梁建军(太原)